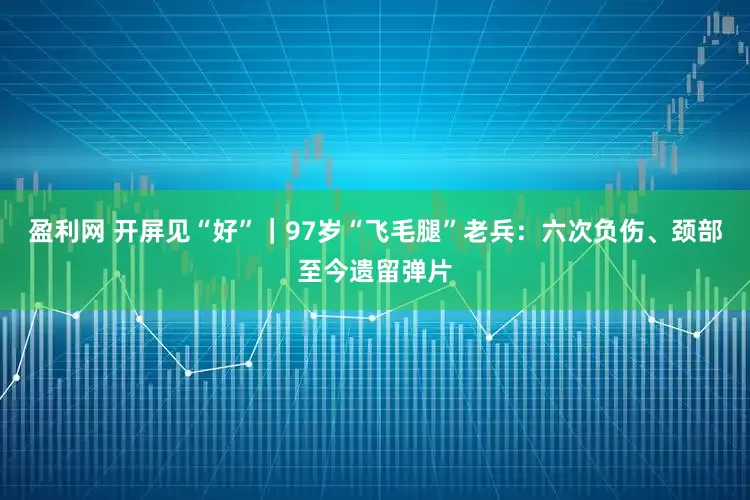

《开屏见“好”》栏目,聚焦山东好人好事,让普通老百姓上封面、上开屏、上首屏,用最突出的位置推介“身边的榜样”盈利网,讲述精彩山东故事。本期人物是“致敬老兵·永不褪色的勋章”系列。

不久前,记者一行前往青岛市市南区的抗战老兵宫健家中拜访,今年马上就满97岁的老爷子有些耳背,但精神头挺好。

“我现在身体还不错,还多亏当年天天跟日本鬼子‘赛跑’,练就了一副硬身板。”听到记者关心自己身体健康的话,他笑呵呵地回应。
身经百战,6次负伤,2次重伤,至今尚有弹片嵌在颈部难以取出,腿上刻有一道道显眼的伤痕……回顾宫健的军旅生涯,那段充斥着硝烟与炮火的经历,显然不似老人轻描淡写的这样轻松。
1928年,宫健出生在烟台市牟平县的一个贫苦农家,家里一共五口人,靠天吃饭,日子过得很不容易。
“1938年,烟台被日军占领了,也是那年秋天,我哥哥跑去干八路了。那会儿我还小,不懂。”宫健说,到了1940年,自己种地时和父亲怄气跑到了山上,正巧遇到八路军招兵。

“对方也是几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,他们问我是干嘛的,我问他们是干嘛的。一听是八路军扩军,我说我也想当八路。”就这样盈利网,12岁的宫健正式加入了八路军。
回忆起刚入伍的时光,宫健记忆犹新。“参军后吃的第一顿饭是面条,吃面条喝面汤,那会觉得吃得真好,难得的一顿饱饭。”宫健还记得,自己入伍第一年的“八一”,部队还准备了猪肉大烩菜庆祝节日、“改善生活”。
“过完节就分配了,年纪小上不了前线,我就被调到东海司令部当勤务兵。”宫健说,14岁又转为传令兵。
宫健跑得快,是队伍里的“飞毛腿”,当上传令兵后,更是发挥出了个人优势。他专门负责在附近几个村子之间跑腿送信,部队里但凡有急件,准是派他去送。

时隔八十多年,宫健还能准确回忆起当时传信用的信号:“插根鸡毛表示事情要紧,插根火柴代表特别紧急,都得赶紧送到。”
1943年那会儿,日军和八路军实力悬殊,正面硬碰硬打不过,宫健和战友们最常用的招数就是骚扰袭击。“扔个手榴弹、开几枪就跑,换地方照样再来一套。等日军来抓人,我们早跑了。”
说到这里,宫健很骄傲盈利网,就是这种“敌进我退、敌退我进”的打法,让日本鬼子整晚睡不着觉,拖垮他们的战斗力。
除此之外,宫健他们还想出更多的“花招”干扰敌人的作战——到田里捉几只刺猬,饿上几天,等时机成熟,就带着这些饿肚子的刺猬和用盐水泡过的黄豆,撒到敌人的老巢里——这活儿实际很危险,得绕过敌人设置的深沟、铁丝网和大铁门,才能把刺猬放到合适的位置。
“刺猬吃了咸黄豆就渴,不光会到处找水喝,还一边动一边咳嗽,‘咳咳’声就跟人一样。日本兵分不出来,机关枪一阵乱扫,整个日军根据地都别想安生。”宫健说,也就是这样的时候,自己人才能勉强睡好一点,“得时刻防止对方偷袭,睡觉也都抱着枪、裹着棉袄,棉袄缝里虱子到处爬”。
抗战胜利后,1946年宫健进入军校学习,毕业后又投入了解放战争中。讲起自己六次“挂彩”,宫健记忆犹新。
“有一回子弹打到了我腿上,没办法就地治疗,只能接着跑,弹头就顺着下去了,等到就医的时候,医生用探针在伤口里找了很久才把子弹取出来。”宫健说,自己负伤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:“我站在坦克上,一颗子弹打在坦克上,又反弹进我脖子里,我当场就昏迷了。”直到如今,这枚子弹仍然嵌在宫健颈部。

问起他当年上战场是否也会害怕,宫健直言,“是个人都会怕死,但上战场,我们身上背着国家的任务,背着我们的使命,也就根本顾不上害怕。”
今年97岁的宫健,由子女每天轮班照顾,采访当天,在家的是他的女儿宫荣荣和宫萌萌。宫荣荣告诉记者,现在的父亲像个“老小孩儿”,“智能手机用得特别好,主要是看新闻,看不清就听,每天都得看很久。”

“现在不一样了嘛。原来我们通信用腿跑,用布条、用电报,现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,一个手机就能联系那么多人,看那么多事儿。”宫健说,通讯工具的迅速发展,让自己这个“传令兵”感到新奇又高兴,“日新月异,日子越来越好了。”
(大众新闻记者 李钦鑫 高广超 石少汛 王培珂 杨帆 编辑 刘宪伟 设计 吕文佳)
方道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